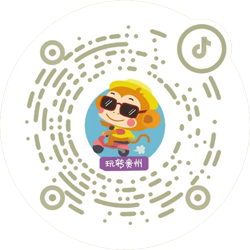【农民日报】四渡赤水 出奇制胜

冬日的赤水河,河水依然湍急,站在群山环绕的贵州土城蔡家沱渡口,人显得特别渺小,不远处的高速公路桥犹如一道彩虹。立于江畔,不由想起《长征组歌》里的那句“战士双脚走天下,四渡赤水出奇兵”。
86年前,中国工农红军军委第一梯队、军委干部团、第5师从这个不起眼的渡口西渡赤水河,演绎了一段中国战争史上的传奇。
1935年,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贵州、四川、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了运动战战役。根据敌情,毛泽东巧妙地指挥部队在国民党重兵中迂回穿插,声东击西,在反复调度军队部署的过程中,成功地摆脱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危局。
四渡赤水纪念馆讲解员杨越告诉记者,遵义会议后,红军原定执行《渡江作战计划》,经习水从泸州至宜宾一线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当时红军前有阻敌,后有追兵,情况十分危急。1935年1月28日晨,红军在青杠坡与川军展开激战。根据事先获得的情报判断,敌人兵力为4个团,但战斗打响后发现,川军参战兵力超过8个团,且有增援部队赶到。战斗非常惨烈,我军部分阵地被突破……危急关头,朱德、刘伯承亲上前线指挥作战,毛泽东、周恩来命令干部团发起冲锋,夺回部分阵地,同时电令红二师从元厚急速回援。
经过反复争夺,红军占领了主阵地营棚顶,伤亡达3000多人。毛泽东等当机立断,指挥红军主动撤出战斗,改变行军路线,准备西渡赤水河。红军连夜架浮桥,第二天凌晨渡过赤水。事后得知,渡河行动再晚半天,红军就可能再次被围……
从1月29日一渡赤水开始,到3月下旬四渡赤水结束,两个月时间内,“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回来了”。遵义会议纪念馆里,陈列着一份党中央、中革军委发布的《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》,对当时的作战有这样的描述:“有时向东,有时向西,有时走大路,有时走小路,有时走老路,有时走新路,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。”
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一个模拟场景里,我们看出,当时原本打算北渡长江的红军在青杠坡遭遇激战,由于敌军的支援部队不断赶来,形势越来越不利,红军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,这便是第一次渡过赤水河。
习水县位于贵州、四川、重庆交界处,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第一渡有两个渡口,就是在习水县的土城古镇。
“当年的赤水河比现在要宽,最窄的地方100多米,宽的地方有300多米。红军想短时间在平均200米左右宽的河面上架一座浮桥,如果没有当地的无私帮助,根本就无法实现。”杨越介绍。
在纪念馆里,记者见到了当年建造的浮桥一段,桥的底下是一条一条的船,桥面则是老百姓的门板或者是其他的木材。
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把敌军主力全部吸引到了川滇边地区,这时贵州兵力薄弱,中央红军迅速转兵往回二渡赤水,向黔北进军,取得遵义战役的大胜。此后根据敌军军情的实时变化又两次渡过赤水河。
四渡赤水是在战略上极为被动的情况下,在红军远离根据地作战的背景下,以3万人对40万敌军的兵力悬殊情况之下,逐步取得了战略的主动权。它是以少胜多、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,也是运动战的典范。
遥想当年,3万红军在远离根据地、连续转战的不利条件下,与40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在贵州这片群山里巧妙周旋,最终走出了困境,赢得了这场双方实力极度失衡的战略博弈。如今,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墙壁上,镌刻着当事人对这场战争的评价。毛主席颇为自豪地说:“四渡赤水是我平生得意之笔。”邓小平说:“毛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,就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!”习近平说:“毛主席用兵如神!真是运动战的典范。”
四渡赤水出奇兵成就红军战争时的光辉典范,而在赤水河畔英勇战斗过的红军战士们,则用生命践行着为了救国救民而不畏艰险、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。
在土城,我们还听到了一个让人感动的红军故事。何木林是江西人,在青杠坡战斗当中负伤之后留在了土城,由于他的口音和当地不一样,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,也为了保护当地的乡亲们,装作一个聋哑人在土城生活。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,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位老红军。
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,我们在土城老街上找到了老红军何木林曾经居住过的房子,现在他的儿媳林成英还住在这里,说起何木林装哑巴的故事,她记忆犹新。
“他的江西口音很重,所以他要装作哑巴,与人交流他用手来比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他才公开讲话。”林成英说。
新中国成立后,何木林被追认为老红军,但他没有对国家提过任何要求。政府给他发的公费医疗本,直到1979年去世也没有用过一次。何老生前只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去世后把它埋在他曾经战斗过的青杠坡,他要和牺牲在那里的3000多名战友永远在一起。
“他总是说自己比别的战友要幸运一点儿,被当地村民救了,多活了几十年。”林成英说,“他一直说他是红军,要求我们这些后人一定要发扬红军的精神,把红军的精神传下去。”